杨福泉、杨琼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云南视角
时间:2025/8/19 10:54:57|点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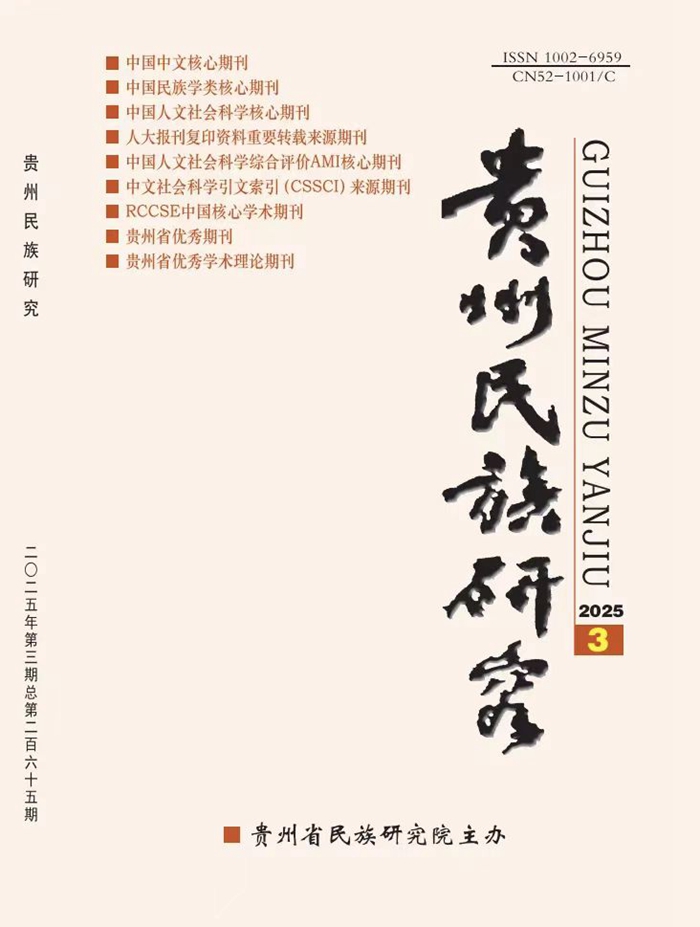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ZDA15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福泉,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学;杨琼珍,博士,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史。
[摘要]:人类在历史上创造与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形成了人类的文明,人类文明集中了世界上各民族和国家的智慧、文化和知识。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文化是文明的基础。中华文化是由56个民族的文化融合而成的。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文章从云南的视角,分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形成的规律和特点,论析了努力学习汉文化而又有创新的云南各族文化;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补、民族地区的文化习俗对汉文化的影响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结合云南经验,论析了如何在互补共生的基础上有创新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云南视角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本文立足于从云南的视角,看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形成的规律和特点,通过总结和审视这些历史的经验和特点,来思考如何在当下促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一、学习汉文化而又有创新的云南各族文化
人类文明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只有交流互鉴,不断创新,一种文明才能充满活力与生命力。云南自古以来处在东亚文明、东南亚南亚文明的交汇地带,是很多族群迁徙流动的重要走廊,各个族群在迁徙中有很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云南各民族不断学习和吸收不同时期的汉文化,而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在生产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云南民族文化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也有长久的交流和交融。各民族不同支系之间也有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互鉴互补,但又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特色。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互补而又极具个性特点的云南文化,它是中华文明史的绚丽篇章[1]。
纵观云南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云南文化得益于云南各民族与中原文化的密切交流,得益于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云南文化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在云南各地区域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汉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云南的区域文化和各民族的文化也丰富了汉文化。南诏大理国文化、元明清时期的云南文化,都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汉文化影响云南不同时期的文化和云南本土文化与汉文化交融而丰富了中华文化。
纵观历史,丽江古城自明清以来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这是促进纳西族近现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明代,纳西木氏土司就积极学习汉文化,能用汉文写出不错的古体诗,有多种汉文诗集,受到中原名士的赞扬并选编入一些重要的书籍中。1723年“改土归流”之后,汉学教育在丽江古城日益普及,除了汉文学对木氏土司的深刻影响之外,汉族的建筑、饮食、医疗、汉传佛教、道教等文化,对丽江纳西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丽江的“改土归流”是清廷在雍正元年(1723)开始实施的,之后,汉文化教育在纳西族中逐渐发展。据光绪版《丽江府志》的记载,在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到清末的180年之间,丽江纳西人考中翰林、进士、举人、副榜、优贡等的考生有200多人。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丽江纳西人考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读书以及赴日、法、美、苏等国留学的,就有好几百人[2]。
中原的汉文化进入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后,与本土文化产生了互动与融合。比如,逐渐产生了汉族的龙信仰与纳西族的大自然神“署”信仰融合的生态文化。纳西人信仰相传与人类是同父异母兄弟、掌管着山林河湖和野生动物的自然神“署”。汉文化中龙的功能和纳西族的大自然神“署”的功能有不少相似点,于是“龙文化”与“署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民间融纳西族和汉族两族信仰为一体的生态文化。
明清时期,纳西人也学习汉族和白族的建筑技艺,把它融入丽江古城的建筑中。木氏土司建造了不少汉地式的宫殿建筑群。但纳西人在接受中原建筑文化之时,也在学习和借鉴中有创新,不忘将它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比如,木府的坐向是“坐西朝东”而非中原常见的“坐北朝南”,因为纳西族喜欢朝向太阳,住宅朝向东方,在纳西族的五行方位观中,日出之东方属木,有希望能得到吉祥的“木”的保佑的观念。大旅行家徐霞客明末来到丽江,他曾记曰:“丽江诸宅多东向,以受木气也。”[3]随着汉文化在丽江的发展,许多纳西人接受了“坐北朝南”为佳的建筑风水文化,形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在汉族传统文化中,有的认为水进入宅院后最好汇集为水塘或水池,认为水会带来财运,财运应想方设法让它留在宅内。溪水流入院内,应该让它贮存在院子里,不应让它流出宅院,让家里的财气外流。纳西人也视水为吉祥之物,但没有这样的观念,丽江古城的不少人家把溪水引入家里,任其自由流淌在宅内外[4]。
木氏土司的府第是学习模仿中原王宫的建筑而建,但没有学王宫位置应“居中为尊”这个观念。木府建在丽江古城的南部边缘地带,而商贾云集的四方街才是古城的中心,纳西话称四方街为芝绿古,意思就是城的中心。许多的街道从四方街延伸到四方八面。这是丽江古城最初形成于位于四方街的乡村集市,之后逐渐繁荣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它与丽江大研古城长期作为“茶马古道”重要集镇的历史有密切关系。
丽江古城的建筑吸收了汉族、白族、藏族等民族的技术精粹,形成融合多民族建筑风格于一体,以中原古老的建筑风格为主调的格局,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认为丽江古城保留了很多唐宋中原建筑风格,他说:“丽江附近建筑,已完全汉化,但较昆明、大理,保存古法较多,且详部手法极富变化。”“犹存唐宋遗风”“(云南)省内中流住宅,以丽江县附近者,最为美观而富变化。”他又说:“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之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廓,适应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也。”[5]
汉文化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产生了有个性有特色的云南文化。这样的结果也丰富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各民族文化互补共生中日益丰富多彩和厚重博大。
闻名遐迩的“海菜腔”是云南彝族民歌,产生于云南石屏,流传至周边建水、通海等彝族聚居地。有滇南四大腔之首的声誉。彝族“海菜腔”的歌词都是汉语,据说过去也有用彝语唱的,后来随着彝族、汉族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以汉语歌唱为主,而曲调则保持彝族音乐风格。
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建镇东莲花村始建于明代中叶,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该村清真寺的建筑是土木结构,风格以中式为主,东莲花村是一个回族村,但在历史的进程中与汉族、彝族和白族相互交流和学习,反映在东莲花清真寺的建筑装饰上,就很有多族多元文化的特色,反映了回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有不少装饰图像体现了多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包容性。东莲花村清真寺这种尊重和保留历史文化真实的做法值得各地回族村镇文化建设借鉴[6]。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纳西族东巴古籍除了与古苯教有密切的关系之外,有的仪式和经书也反映了汉文化对东巴文化的影响。比如东巴经中也有祭城隍、退白虎等受汉文化影响的内容。比如有本东巴经核心内容反映东巴文化中的祖先文化观念。经书称死者为斯蹦祖先,祈求年岁和寿岁、贤能和快捷、生育和繁衍、富足和富余的思想,祈愿上方祖先欢欣、下方家人生育繁衍和健康长寿等思想,与纳西族传统东巴经典文献思想意识形成一致,也是汉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民族化的表现。为墓碑石刻动物点血、献药,则是汉文化经语的直接译用[7]。
笔者不久前到鸡鸣两省(滇川)四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香格里拉市、木里藏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的宁蒗彝族自治县拉伯乡获得中国传统村落荣誉的油米村调研,这个村大多是纳西族汝卡人。油米村周围的村子有普米族、汉族、藏族、傈僳族、苗族等杂居。汝卡人与汉族、藏族、普米族等民族交往很多,相互通婚。因为这种多民族的亲密交往多,所以很多村民能说多种语言。村里的东巴精通汝卡母语和东巴象形文字,也都能讲流利的汉语。如杨扎实东巴能听懂我说的纳西语西部方言,也能用流利的云南汉语方言和我交流。在他家神圣的母屋火塘边,既有东巴文化的各种图像和面偶,但也挂着汉文化中龙的画像,还挂着道教的太极图。
二、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增添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
纳西族民间音乐套曲“白沙细乐”,在纳西语中称为“伯石细里”(bbesheeqxilli),历史上记载这是蒙古人留下来的音乐。相传在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国,在丽江“革囊渡江”,纳西酋长麦良审时度势,到奉科金沙江渡口迎接他,与忽必烈结下深厚的友谊。忽必烈在分别时赠送给他一支蒙古宫廷乐队。因此“白沙细乐”又被称为“别时谢礼”。该套曲后来流入纳西民间,并与本地音乐相融合。
据学者研究,白沙细乐乐队使用的古老乐器苏古笃(色古笃)即火不斯(胡拨四),原是古代中亚地区的弹拨乐器,苏古笃(即胡拨)的传入,是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由蒙古大军带入。元代芦管的孔数与“白沙细乐”所用芦管的孔数相一致。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些音乐史专家对“白沙细乐”这套组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白沙细乐”融合了纳西音乐和蒙古音乐,是我国特有的几部古典管弦乐之一,其珍贵之处是丝竹合奏,其旋律与“和声”的独特。它具有重要价值,在音乐界有“活的音乐化石”之誉[8]。
东巴古籍的内容融合了纳西族、汉族、藏族等民族多元文化,成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融合进新内容的中华文化瑰宝。其中突出的一大特色,是藏族的本土宗教苯教与纳西族东巴教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后来传入的佛教对苯教的排挤和影响,大量的佛教内容逐渐进入了苯教,古苯教很多的内容逐渐湮灭。而很多古老的苯教内容则留存在与古苯教有密切关系的东巴教中。曾多年从事敦煌古藏文写卷研究的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经过比较研究后认为,东巴古籍中所看到的古苯教的内容,要比支离破碎的敦煌藏文写卷要详细和清楚得多[9]。笔者曾根据国外学者翻译的藏文资料写成《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一文,曾引起很多反响,敦煌学界将它列为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发现,由此也可见古苯教与东巴教关系之一斑[10]。
唐代吐蕃苯教对纳西族东巴教的影响首先肇始于吐蕃上层崇信苯教之时,它是通过吐蕃经营西南时影响到纳西宗教的。麽些(纳西)人受吐蕃统治达百余年,受吐蕃文化的影响比较深。纳西人有认为天地是自然形成的宇宙观。很多东巴古籍中记载,在天地还没形成之前,上面首先出现了吉祥之声,下面产生了吉祥之气。声与气交合变化,出现了天和地,出现了高山河流与日月星辰。东巴古籍在提到与具体地域相对应的“天”与“地”时,常常说这是祖先或祖先神开辟的。在纳西语中,迄今“美堆”(meeddiuq,直译即“天地”)这个词还用来指一个社区(村寨或城镇)的地域。在东巴古籍中常常这样提道:“开天的是盘神,辟地的是禅神,藏族是盘神的后代,白族是禅神的后代”“藏族的盘神威力大,白族的禅神威力大”,然后才说“纳西的吴神威力大”。
这个说法是纳西人曾先后受吐蕃、南诏和大理国管辖的历史的反映。在唐代,麽些人所居住的区域曾经被吐蕃统治,因此藏族的神“盘”(Perq)成了这个“美堆”(天地)的统领者。东巴教中4个主要神祇的排列次序是“盘禅高吴”。“盘”是藏族之神,东巴经中说“古孜盘本波”,意思是“藏族盘神之巫师”;“禅”(Saiq)是白族之神,东巴经中说“勒布禅本波”,意为“白族禅神之巫师”;“高”是胜利之神(战神),东巴教有隆重的“祭高神”仪式;“吴”(Wuq)是纳西之神。东巴经中说“纳西吴本波”,意为“纳西吴神之巫师”。纳西“吴”神与古羌人首领“无弋爰剑”有关[11]。
国际著名学者、藏学家朱塞佩·图齐教授长期在藏族聚居地做田野调研,对藏地的苯教文化很熟悉。他是最早意识到纳西族的东巴教与古代苯教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在为洛克的《纳西——英语百科辞典》写的序言特别强调了东巴教的研究对深入研究古代苯教的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11]。民间歌舞“勒巴蹉”(lerqbbaco)流行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鲁甸、巨甸等地。塔城乡是在公元七世纪以来就受到藏族文化影响较多的地区。这个独特的舞蹈把藏族和纳西族两个民族的舞蹈融汇于一体。笔者20世纪90年代在塔城乡调研时,塔城的老人曾告知,在跳“勒巴蹉”时,当地男子常常会穿上藏装,并用藏语唱歌。这个民间舞蹈最初源于藏族,在纳西族地区流传的时间长了,纳西人将本族的歌舞艺术也融进其中,最终形成了兼具两族舞蹈特色的独特舞种“勒巴蹉”,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各民族在文化交流中互学互补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结合自己区域的地情、民情进行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的成功路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笔者曾经到大理州洱源县郑家村调研,该村村民中有汉族、白族、藏族、傣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七个民族,各个民族各展所长,相互扶助,比如白族的农作物种植技术高超,其他民族向白族学习;藏族村民擅长茶马古道上的经商和药材采集和种植,亦影响了其他民族。滇南地区有居住在坝区和山区的不同民族结成“牛亲家”的习俗,两族根据山上的村寨和坝子村寨农忙的时间差互助协作,驱牛赶马相互帮忙。这是各民族非常有特色的一种互助协作方式[12]。
云南各民族都有蕴含了传统的生态智慧和呵护自己生存的环境的习俗,各民族齐心协力守护生态环境是云南的突出特色之一。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拉伯乡,有汉族、普米族、纳西族、傈僳族、苗族、壮族、藏族等民族。拉伯乡的各族人民坚定地保护森林,森林覆盖率达79%,是宁蒗自治县森林覆盖率最高的乡。拉伯乡已经对境内3.2万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做了登记造册,进行了有效保护。拉伯乡历届党委、政府和民众历来重视保护好森林,经过干部群众多年的努力,换来了今天这样森林茂密,山青水绿的好气象,形成了长江上游的一道绿色屏障。
笔者在迪庆州做田野调查时,多次听老人说道,人生活着就需要自然资源,为了解决既保护山又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矛盾,当地的藏民很早就有个习俗,制定了“日卦”封山线,依海拔高低、距村庄远近等标准,为每一个村子的山林划出一条线,这条线以上为封山区,禁猎禁伐;这条线以下为资源利用区,既可打猎亦可伐木。在迪庆,其他民族也恪守着这个保护生态环境的封山线和封山区的习俗[13]。
最近笔者到宁蒗彝族自治县拉伯乡调研,拉伯乡拖甸村委会三江口村是个多民族嵌入式居住的典型村子,村中有普米族、汉族、纳西族混居。该村著名东巴石春也能讲流利的汉语、汝卡语、普米语、彝语,在逢年过节或有婚丧之事时,常常被远近的其他民族请去举行祈福的仪式。这与三江口的纳西族汝卡人平时就与周边的汉族、彝族、普米族、傈僳族等民族有密切交往相关。
三、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共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需要立足中国的历史积累、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促成,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各民族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14]
云南经验是中国经验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云南的国际文化和学术交流历来都很活跃。改革开放之后,云南通过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传播了我国的民族文化和新中国扶持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和做法。云南在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和民族文化强省的过程中,对世界了解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做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丽江古城文化的形成中,突出地反映了汉族和纳西族的相互影响的特点。除了汉文化深刻影响纳西人这一点之外,纳西人的一些良好习俗也影响了汉族移民。比如,纳西族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很突出,她们没有缠足陋习。她们这种人性化的习俗对明清时期来到丽江的汉族移民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绝大多数古城的汉族移民女子都不缠足。她们与纳西族、白族、藏族等民族妇女构成了以敢作敢为吃苦耐劳而闻名的丽江女子群体。
纳西族的习俗是青年男女可以自由交往,谈情说爱,社交公开,这种本地习俗对丽江古城的汉族移民也有影响,冲淡了“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等儒家礼教的观念和习俗,在古城,青年男女是可以公开社交的,青年男女可以一起打跳、跳火把、逛庙会、灯会。清代一些派来管理丽江的汉族流官长期囿于封建礼教的熏陶,曾制定了禁止妇女参与庙会、灯会、禁止青年男女在这些场合“混而无别”地社交的条例[15]。但受到纳西族男女自由社交习俗深刻影响的古城汉族移民仍然保持了传统的符合人性的良好习俗。
笔者2022年在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头白族乡利苴村委会调研时也了解到,当地的傈僳族传统的葬俗是火葬,但也和纳西族一样,在清代被官府强迫土葬,所以他们早已经改为土葬。随着现在政府推动殡葬改革,提倡和鼓励火葬、生态葬,并发放相应的补助,使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开始恢复火葬习俗,但如今他们已经不会操作火葬了,而当地彝族一直恪守着火葬的传统习俗,于是他们就请来彝族朋友教他们如何进行火葬。这也是国家的政策逐渐推进移风易俗,各民族之间齐心协力进行风俗改良的一个好例子。笔者想,当下中华民族文明的建设,是需要扎扎实实从这样的小事上做起,做到实处,天长日久,必然会汇流成川,形成去芜存菁、与时俱进、贴近人心、裨益民生的当代中华文明。
云南纳西族、白族等民族很早就接受了汉族的京剧、滇剧等艺术。近年来,以《纳西三部曲》为代表的云南少数民族的“打跳”音乐在内地和边疆地区十分流行。各民族艺术的交流与融合日益普遍。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和镇是一个汉族、纳西族、傈僳族、白族等多民族混居的古镇。笔者在维西调研时,获悉此地长期以来流行一种地方戏剧,当地称为“大词戏”。这是内地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戏种。清朝时,这个剧种被来自内地的绿营兵带到了维西。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与维西本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产生了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维西大词戏。维西本地的地方语言和民间音乐因素融进了大词戏,大词戏吸收和借鉴了当地各民族的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在一些戏的唱段中借鉴了纳西族和汉族的山歌小调。又如在一些角色的表演动作上就吸收了藏族、傈僳族的某些舞蹈成分,效果很好[16]。笔者曾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看过大词戏的演出,注意到很多演员穿着传统的纳西妇女服饰。据了解,这是唱大词戏的传统习俗,而演唱的却是来自汉地的古老戏剧,从中可看出这种外来的汉地艺术与本地少数民族艺术的融合[17]。
四、创新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传承的结果,它既融汇了各民族文明的精华,又超越了各民族文明的具体形态,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生成的。现代化的本质是文明创造和文明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是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18]。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会发生变化。每个时代都需要充满活力的新文化诞生,都需要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营造当代文明。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在努力创造自己充满个性特色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如“七彩云南”“多彩贵州”的多元文化之美,给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中华文化的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民间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的民族文化艺术不断在国际上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1959年,反映大理白族生产生活与爱情的电影《五朵金花》是新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优秀影片,在46个国家公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纪录。又如撒尼人的民间史诗《阿诗玛》先后被翻译成七国文字,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学名著而享誉文坛。两部作品抓住了爱情、喜剧以及神话史诗的瑰丽神奇内容,其中的音乐也非常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各民族的文化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扇独特的窗口。云南的少数民族古籍抢救和整理出版工作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经过20多年的努力抢救而译注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荣获国家图书荣誉奖,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丽江收藏的东巴古籍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记忆名录”桂冠。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充分发掘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影视剧和歌舞的再创作,催生了一批民族文化精品。如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导演兼主演的歌舞剧《云南映象》,其演员70%来自10多个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也保留了云南各民族的本真特色。改革开放后,丽江大研古乐队摒弃了女子不能参与演奏的传统,吸收了好几个女乐手和歌者,推陈出新,别开生面。该乐队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应邀到近30个国家演出。2007年10月为庆祝第62个联合国日,丽江大研古乐队受联合国驻华机构之邀,10月22日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了为联合国庆生的专场演出。
云南美丽多彩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民族文化在世界上闻名遐迩,给无数慕名而来的客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的国际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尤其以民族学与人类学为世人瞩目。云南的学者不断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国进行学术交流,很多国外的知名学者也来云南学习和进行田野调研,国外很多大学的学生来云南研学。很多国际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与中国合作,在云南举办了不少聚焦民族文化和学术的国际会议和文化展览。云南民族文化不断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绚丽多彩的文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国家争了光,向世界展现了我国坚持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民族文化保护、抢救和传承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笔者作为云南学者的一员,也多次应邀到欧美和东南亚国家讲学,云南基于在基层社区的保护传承和保护发展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与旅游的互动融合,受到了国际学术文化界的高度赞誉。
云南在可持续地做好当代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方面,也做出了独有创意的努力,有的被誉为“中国经验”。比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构成部分的束河古镇和文林村,多年来探索出了一种有创意的发展模式。两个村子在村落的核心区外围建盖了保持本地传统建筑风格的房子,作为古村落的一种拓展,严格地保护了村落的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村民们留居在村子里,保持了传统的日常生活习俗。游客在村里可以看到纳西族农民真实的日常生活、纳西民俗和田园风光,和本地人一起过节同乐。学者们将此种模式称为“分区制”,它避免了原住居民大量外迁导致的文化流失,保持了“人村同在”的格局[19]。
五、结语
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对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焕发勃勃生机与活力的见证,而云南各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的互学互鉴、互补共生的过程,也形成了从中可以看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形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性与共生性的一扇窗口。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和人类发展的重要动力。各民族需要相互学习,学人所长,补己之短,这样才能建构起现代文明建设。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我们首先要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史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剖析,对构成中华文明史的我国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总结,对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如何相互学习交流和融合,逐渐创造出互补共生、充满活力的中华文明,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形成的规律、特点和优势。云南多元一体的灿烂文化,也增进了我国对外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和对外传播内容的丰富性。
我们当下深入论析云南各民族相互借鉴又有创新地建设而成的文化与文明史,深入探究云南各族文明在融入中华民族文明的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云南各民族如何在相互学习和借鉴中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和繁荣发展;云南在中华民族文明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以及研究当下面临着如何建构新的具有创新性的现代文明挑战和问题,这对我们怎样在互学互鉴、互补共生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杨福泉.“云南文化史丛书”简评[J].今日民族,2021,(12):50.
[2]张大群.略论丽江纳西族历史上的学校教育[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6):88.
[3]徐霞客游记校注[M].朱惠荣,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930.
[4]杨福泉.纳西族文化史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474.
[5]刘敦桢文集:第三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187+334.
[6]张春继.云南东莲花清真寺屋脊神兽研究[J].装饰,2019,(10):139.
[7]杨福泉,杨杰宏,和力民,等.东巴文献及其当代释读刊布和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8.
[8]何昌林.国宝埋藏在喜马拉雅云岭深处——为丽江纳西古乐团晋京演出作[J].人民音乐,1993,(11):24.
[9]石泰安.敦煌吐蕃文书中有关苯教仪轨的故事[G]//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四辑.岳岩,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202+235.
[10]杨福泉.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J].民族研究,1999,(1):92.
[11]杨福泉.东巴教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558-560.
[12]杨福泉.新定位大团结——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纪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344-354.
[13]林红,刘怡然.鹿行九野: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38-247.
[1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知,2023,(17):6.
[15]杨福泉.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133.
[16]张秀丽.维西大词戏[J].民族音乐,2008,(6):35.
[17]杨福泉,杨琼珍.跨族际艺术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以纳西族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72.
[18]陈金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特质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23,(8):16-21.
[19]杨福泉.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丽江经验论析——基于田野民族志的个案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17.
来源/作者:贵州民族研究 责任编辑: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