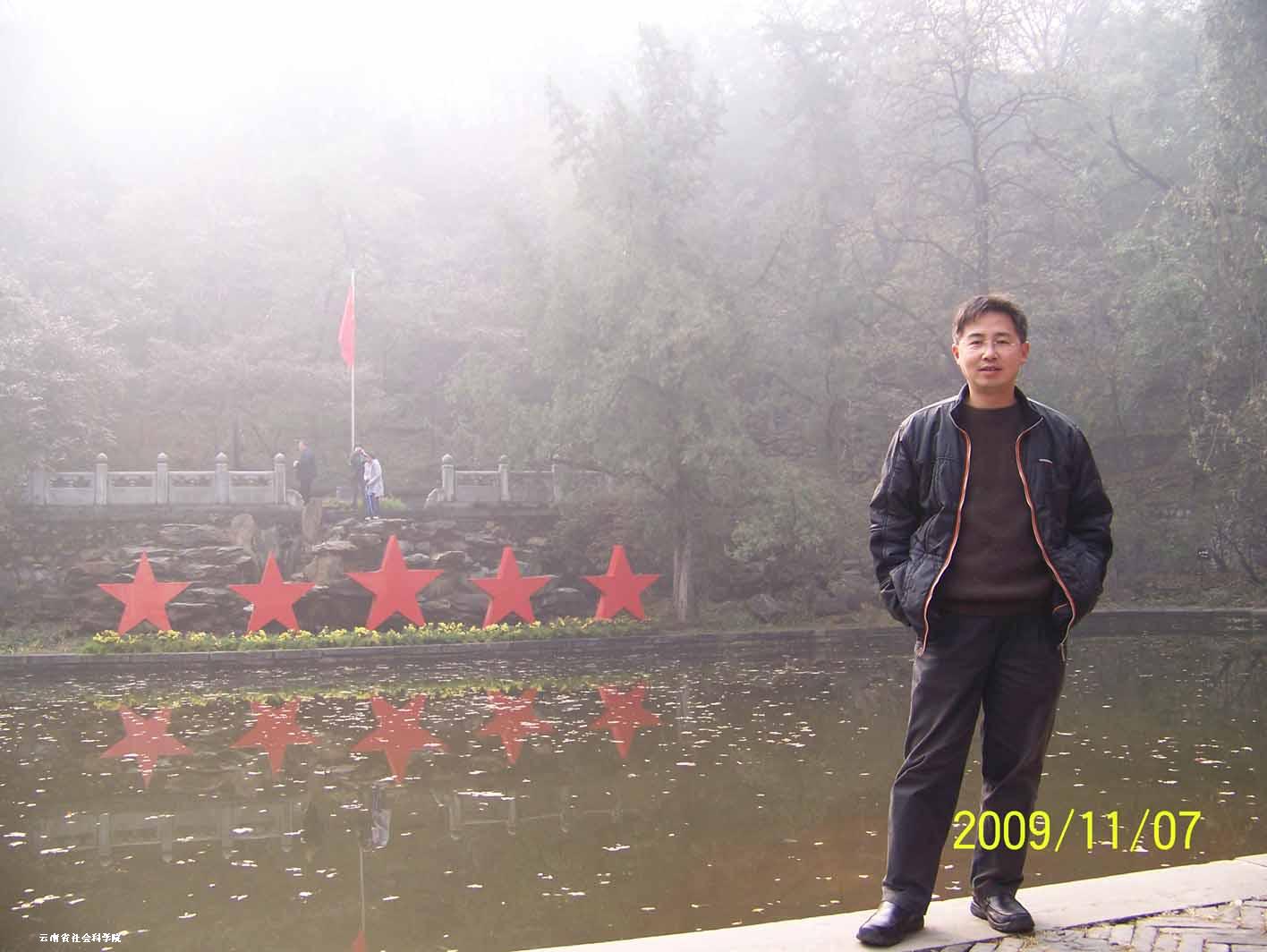2009年作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期间在北京香山“1949年中央机关旧址”
每一个当代,我们都感到必须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同时呈现两端极点的交错混杂才能表达出时代强加给个体感官的巨大张力。而我们今天的不幸在于,虽然托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鸿福我们已经可以坐享其成地轻易占有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神文化精品,但身体的智能处理“湿件”却并没有因此就比我们石器时代的先祖进化多少。此际,人人都恭逢盛宴,而无一不怀揣羸弱的肠胃。“是”与“有”的鸿沟空前巨大。少数胃口健硕者一如叫花子进城,逮啥拿啥,其结果有二:要么患上精神的消化不良症,在堂皇体面的文本输出中吃啥拉啥;要么患上思想的感官疲劳症,在生活思考的滔滔叙事中撑死于前,噎鲠于后,既麻木了精神,又麻木了物质。更大的悲哀在于,我们中的很多人由于生活的压力,甚至已经丧失了暴殄天物的兴趣与食欲。
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从大学课堂里舀来的理性之水以及在书本里所呈现出的人的主体尊严,在步入社会之际刹时荡然无存,因为那些早已在人们熊熊的物欲之火中瞬间蒸发干净了。这也是当初作为愤青的马克思所遭遇、所郁闷,并斥之为“下流的唯物主义”的境遇。背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像阅读唐宋传奇一样旁观着一个个太平盛世的眩目文化景观。然而,传奇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米兰·昆德拉式的矫情,乔治·奥威尔式的冰冷,于丹、易中天式的闷骚,乃至哈贝马斯式的絮叨。思想反省物化的努力,总因现代物化现实所附着的魔力和其他生活中的“一地鸡毛”而日渐褪色。
学术乃天下重器。社会科学,肩负着现实思考与批判的责任。然而,批判的姿态因其无知所以无力,思考的探寻因其无力所以无果。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不能使各种思想理论对自己产生精神性的诱惑力,那我们的研究就不是一种足够好的研究。如果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还没有产生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好生活的内容,无非就是权位、财富和生殖。这些本是无可厚非的欲望,但是学术的责任需要我们的学习更进一步:废除学习作为我们时代的幻想的幸福的神话,就需要我们能够在学习中实现自己的现实的幸福。在一个知识极大爆炸并且教育早已不是稀缺物品的时代,“知识改变命运”已经越来越被证谬为实用主义的文化座标:一轴编织着信息社会与古老价值体系杂交的神话,一轴则指向商品成功学意识形态的幻象,其趋势曲线图终将导向学习的虚无。而沿着这条学习的虚无道路走下去,又有两条分叉:一条是“学而但思其物”,由形而上学学科体系的概念拜物教直接进入功利拜物教的主战场,其结果是“我用青春赌明天”的当代世俗宗教;另一条则是更加可怕的“不学无思”,因为在竞争时代中,“不学无思”明显地彰示着明天不可避免的物质贫困,以及今天日常心情中的精神栖遑——“娱乐至死”并非来自大洋彼岸的后现代谶言。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并且我们的学习不耻于为当代“布波”的恶俗格调所标示。
学什么?怎么学?当然是读经典。知识并不必然改变命运,但,思想却可以改变人生,至少可以改变生活的色调。知识经济时代,其直接的含义是财富的创造已经越来越依靠知识的创新与增长的时代,间接的意思是知识已经成为可以直接创造财富的产业化的时代;但知识经济时代的另外一个意思,按照安布罗斯·比尔斯的解析视线,知识经济时代难道不是一个知识已经变得非常“经济”的时代吗?拥有经济实惠、随手可得的资源难道足以改变命运吗?所以,作为当代学人,我们必须首先实现自身对于知识看法的格式塔转换。学习,非为功利目的做知识的攀登状或学术的高深状,因为知识总会因其过时而腐败变质,学术也会因空洞无力而蜕变为拜物教的另一种游戏。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大师们的思想方法。只有贴近大师们的思考原点,把以前在教科书或普及性读物中被定制化、被曲解的内容悬搁起来,把原先已经受到的通识教化置之度外,把以前囫囵吞枣圐圙不化的印象先放一放。静下心来慢慢地仔细研读经典原著,不求其快,不厌其精,用一种再陌生化的态度把经典当作一种自己毫不熟悉的东西,来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入门者,再通过研讨,互相证悟。
哲学使人睿智,学习使人恭谦,阅读使人快乐。

2004年在南京大学

2006年春在武定县作民族宗教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调研

2008年在寻甸县红色庄园开院工作会
(责任编辑:秦伟)